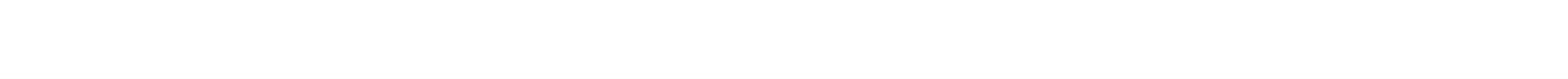乡村大碗菜
王长敏
厚道的乡村人为了表达对客人的热情,都尽量用大碗盛菜。
在我年少的时候,家里来了客人,母亲到厨房做菜之前,会掐着指头算,数到八个,我就知道,她要做的是大碗菜。
碗是粗糙的大口碗,土黄色。那时候,家家户户都备有一些大碗,以免客人多了,还要跑到邻居家借。
每逢过新年,亲戚们都要走动。母亲为了做好这八碗菜,在春天的时候就开始准备。在贫穷的岁月,这八碗菜着实让母亲煞费苦心。
我的母亲读过私塾,懂得一些待人接物的礼仪。她常说,人混脸,树混皮。她还说北瓜是不能上餐桌的,在乡村人眼里,北瓜到处丛生,一棵瓜藤,就会结出几个大瓜,这卑贱之物,不能登上大雅之堂。还有豆芽不能上桌,不管是黄豆芽,或是绿豆芽。
一次,父亲外出做生意,遇到香椿树苗、花椒树苗、黄花菜根,就带回来。母亲把这些小苗儿栽种在阔大的院子里,她精心地照顾着这些稀罕之物。
到了春天,黄花菜开花,母亲在花苞还没有完全打开就掰下来。在热水里焯一下,一根根摆在木板上。等晒干了,就装进棉布袋子里。
到了夏天,母亲开始晒茶豆,她每天早晨把带露水的茶豆摘下来,放进锅里煮,要煮熟,这种皮厚的菜,煮烂一点才好吃。
然后,把茶豆一片片摆在锅盖上晒成干菜,包装起来。到了春节,家里来了客人,母亲拿它们做油炸菜,这种干菜,泡软,挤干水,拌了面,放进茴香粉,在油锅里炸,不管是猪油,或是棉籽油,都会像炸焦的小鱼一样好吃。
春节期间,不管来多少客人,就是来一位客人,也要做八碗菜。这八个碗,一定有炸丸子、炸莲菜、炸肉,这些早已炸好的菜食,等客人来了,就装进笼子里蒸。
剩下就是炒热菜,炒豆腐,炒红萝卜掺鸡肉或羊肉,花肉片炖粉条,凉拌莲菜和芹菜。还要熬一锅清香的白米粥。
等到把饭菜、白馒头端到桌上,客人们按辈分的高低坐下,母亲不停地给客人夹菜。我们小孩子一般是不允许坐桌吃饭。白馒头只给客人吃,如果我们坐桌吃黑黑的杂面馒头,客人会不好意思的;再就是怕我们食相难看,看到好吃的就止不住吃个没完没了。所以,我们只能待在厨房里慢悠悠地吃饭,等待着从餐桌上撤下来的剩菜。
这些美味在我往桌上端菜的时候,香味就经过我的鼻子,让我对美食产生无穷无尽的幻想。
客人们一边吃饭一边聊天。在我们急得不耐烦的时候,母亲才把桌上的菜端回厨房。菜大多凉了,已没有刚出锅时的味美了,母亲要陪客人聊天,也不再给我们热菜了。只有等到下顿,母亲把所剩的菜全部倒进锅里,加一些水,煮得热气腾腾,算是大锅菜,味道虽然不错,但我没有多少兴趣。我盼着走亲戚上桌吃,可这样的机会总是轮不到我。
我经常看着从我村田野间穿越而过的穿得花花绿绿的少男少女。我眼睛不眨地盯着他们,一直等到他们走进另一个村庄才收回目光。
等到我过了十二岁生日,才到离家十二里路的姨妈家去走亲戚,第一次得到了压岁钱,还吃到了餐桌上的美食。
我发现我姨妈和我母亲一样,把白馒头放在屋梁上吊的竹筐里,这样,贪吃的小孩子是够不到的。
我姨妈的厨艺不错,她炒的酸辣白菜、红萝卜肉丝比我母亲做得味美,她蒸的白馒头好看又好吃。
我津津有味地吃一顿美食,像圆了一场美梦似的。回到家里,向伙伴们炫耀了好一阵子。
有一年,外出做生意的父亲回到家里,把挣回来的钱,全部上交给生产队,没钱买肉、买菜。我的母亲满脸愁苦,她连连哀叹:“年好过,月好过,穷日子难过。”
我的爱面子的母亲,认为没有美食招待客人是丢人的事情。父亲没有办法,只得冒着寒冷去外乡拉回来一车甘蔗,我正好放寒假,就跟着父亲去卖甘蔗。在春节前,我们就挣了一些小钱,母亲拿去买了一些猪肉,只能紧巴巴地招待客人,所以,我们过年吃的饺子,馅里包的是炼猪油的油渣。
后来,生产队解散,责任田分包到户,我家分到了十几亩田地,屋子里有了粮仓,也在田间或地头种一片蔬菜瓜果。
有了多余的粮食,就可以养猪养羊养鸡。我们每年过春节,都要杀猪宰羊,还要杀几只公鸡。
新鲜猪肉用麦秸火烤了,晾晒在屋檐下,或者把肉放了盐做成腌肉,放进罐子里,过一段时间拿出晾一下,免得坏掉。这些肉食,是一春一夏的美食,除了招待客人,还有多余的自己享用。
在我十五六岁时,也学会了做大碗菜。打麦时我们要请村民们帮忙,母亲就让我做菜,她一定要让我做八碗菜,我就像母亲那样,计算着每一道菜要做什么。
那天,我算来算去,还是少了一道菜。屋里已经没有多余的菜了,我就把白菜心剁碎,打入鸡蛋,炒成清香可口的菜,帮我们打麦的村民都说好吃,但是吃不出来是什么菜,他们直夸我的厨艺好。
乡村的大碗菜,一直牢记在我的心里,在那些贫穷的岁月,村民们喜欢用大碗做菜,表达乡村人人穷志不穷的精神。不管自己怎么节约,一定要让客人吃好,不能亏待客人。还要懂得哪些菜能上桌,哪些菜不能,不能让客人笑话。
乡村人的美德深入我的灵魂,我懂得了与人交往要厚道,不损人,不坑人。
编辑:徐冬梅 校审:贾红英 责任编辑:张中科 监审:黄术生
上一篇:新春走基层 | 剧团进乡村 群众乐开怀
下一篇:没有了